|
樂器 |
南胡 |
大廣弦 |
殼仔弦 |
鐵弦仔 |
|
內/外 弦 |
5/2 |
2/6 |
6/3 |
3/7 |
|
B-flat /F |
F/C |
C/G |
G/A |
|
|
音域 |
5→6 |
2→3 |
6→1 |
3→5 |
|
C→D |
F→G |
C→E-flat |
G→B-flat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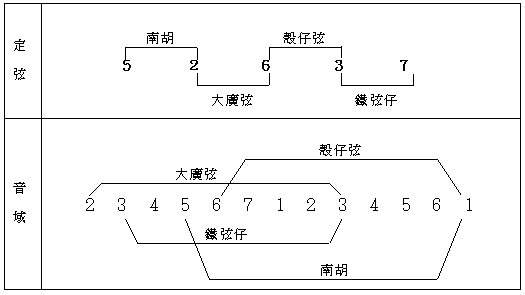
試析歌仔調【慢七字】的四種胡琴伴奏
蔡振家
摘要
臺灣歌仔戲的主要曲調【七字調】,其唱腔與伴奏皆變化多端。如在【慢七字】曲調中,各種樂器以各自的語法(idioms)來伴奏,本文針對四種胡琴:大廣弦、鐵弦仔、殼仔弦、南胡,引用Schenkerian多層次分析的方法來比較其伴奏旋律,以prolongation與級進下行的觀念來探討伴奏的支聲複調現象,從而發現【慢七字】的「唱腔╱過門」中tonic-dominant polarization的深層結構。
摘要
一、前言
二、【七字調】的胡琴伴奏
(一)【七字調】的速度變化、唱腔與過門
(二)四種胡琴的定弦與音域
(三)「支聲複調」(heterophony)與idiomatic style
三、托腔與prolongation
(一)Prolongation——synthesizer伴奏
(二)胡琴的托腔音型
四、過門與級進下行
(一)Conjunct-descent-embellishment——薩克斯風伴奏
(二)胡琴過門中的骨幹音
(三)胡琴過門中的級進下行
五、Middleground與Background
(一)鑼鼓與終止式
(二)支聲複調與多層次(multi-layers)分析
(三)Concertato medium與tonic-dominant polarization
六、結論
七、參考資料
一、前言
本文的研究主題【七字調】,是臺灣歌仔戲的主要曲調,其唱腔素以變化多端著稱,它那不凡的戲劇表現力,與曲中的文武場伴奏有很密切的關係。一個戲曲唱腔板式的構成,除了唱之外,文場的伴奏也是極其重要的一個要素,然而在近年數量頗豐的臺灣歌仔戲著述中,關於文場的研究僅只於樂器介紹,未就演奏做實際的探討。從伴奏音樂的角度來分析【七字調】,可以觀察到單從唱腔分析中無法窺見的一些面向,對於瞭解此曲的深層結構應該是很有幫助的。
筆者曾經先後學習歌仔戲的司鼓與胡琴伴奏,在數年的看戲經驗中,深深體會到歌仔戲文場藝術的博大精深,民間藝人從口傳心授的音樂傳承與長年演出的舞臺實踐,澱積而出的濃郁「歌仔味」,似乎蘊含著許多奧妙的變化。例如【七字調慢板】(簡稱【慢七字】)此曲由民間一流樂師伴奏時,大廣弦、鐵弦仔、鴨母笛、月琴等樂器以不同的旋律、語法各自歌唱,富有民間音樂靈動而飽滿的生命力,遠非看譜演奏的國樂團所能企及。
由於筆者在歌仔戲文場中專攻的樂器是胡琴,因此特別留意歌仔調中各種胡琴的伴奏。從民國八十五年底開始針對「民權歌劇團」所做的田野調查,更使我對於歌仔戲的胡琴藝術有了進一步的體會,本文所引的音樂實例,便以民權歌劇團的野臺戲演出錄音為主。
歌仔戲的文場伴奏樂器以胡琴為主奏,但其與京劇中以京胡為主奏的情形略有不同,京劇中的文場領奏,使用的胡琴只有京胡一種,反之,歌仔戲的胡琴種類多達四種,依據戲劇情境與曲調音樂的不同,主奏者(所謂的「頭手弦」)可能拿起殼仔弦、大廣弦、鐵弦仔或南胡等來演奏,由於定弦、演奏的指法、樂器的音域各自不同,伴奏的旋律也各具風貌。從【慢七字】的伴奏音樂中,可以探討不同的樂器在處理同一段音樂時,各有怎樣的旋律變化,而岐異的音樂處理背後,又有著什麼共通的深層結構。
本文並不打算對【慢七字】全曲作完整的分析,而是著眼於觀念的提出,尤其欲從實例中驗證運用Schenkerian分析方法的一些可能性。J. Stock在The Application of Schenkerian Analysis to Ethnomusicology: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.(1993)文中,以Schenkerian分析方法來研究越劇與京劇等中國戲曲的唱腔,對本文的寫作多有啟發。
二、【七字調】的胡琴伴奏
(一)【七字調】的速度變化、唱腔與過門
【七字調】因速度之別而有【七字調快板】、【七字調中板】、【七字調慢板】之別,其間的界線並非本文探討的重點,在此僅欲指出,從快板到中板,及從中板到慢板之間,與其說速度上有絕對、清楚的分野,不如說它們是基於戲劇表情的不同。
我認為【七字調】並非典型的板式變化體,而屬於較單純的「速度變化體」。與典型的板式變化體(如西皮二黃)比較,【慢七字】過門的小節數與【緊七字】一樣,前者只是後者的增值,沒有像【西皮慢三眼】發展出長篇的花過門,也沒有成熟的【流水板】、【搖板】、【散板】,甚至板腔體中的上下句結構、行當的唱腔區分等特徵,【七字調】也都不夠充分,因此,我稱它是速度變化體。(註一)
以下簡單介紹【七字調】唱腔與過門的形式。基本上,一首【七字調】有四句七字的唱詞,其過門的插入點如下:
□□□□(過門)□□□,□□□□□□□(過門),
□□□□□□□(過門),□□□□□□□,(疊唱尾句)(尾奏)。
這三個過門的旋律是一樣的,其中第三句末的過門有時省略。
前奏有多種形式,省略前奏亦屬常見。疊唱尾句是收束唱段的形式,若要接唱下一首【七字調】,則不得疊唱尾句。
(二)四種胡琴的定弦與音域
【慢七字】常用的伴奏胡琴,傳統上有四種,即殼仔弦、大廣弦、南胡、鐵弦仔(喇叭弦)等,其內弦與外弦間的音程皆為完全五度。由於各樂器的大小、性能不同,其定弦與音域也有高有低;由於四種胡琴內外弦定音的不同,演奏者在用不同的胡琴伴奏【慢七字】時,左手便必須使用不同的指法按弦,如殼仔弦伴奏【七字調】時用「士工管」、大廣弦用「乂士管」、鐵弦仔用「工乙管」等,就是分別將內外弦當作首調唱名的「La/Mi」、「Re/La」或「Mi/Si」,民間樂人稱此為不同的「線路」。
民間樂人以南胡伴奏【慢七字】的指法,跟一般的國樂人士不同,他們會把南胡定弦調為比殼仔弦低一個全音,以「合乂管」(Sol/Re)演奏。
以下將歌仔調【慢七字】胡琴伴奏的四種樂器及其定弦、音域整理為圖表:
|
樂器 |
南胡 |
大廣弦 |
殼仔弦 |
鐵弦仔 |
|
內/外 弦 |
5/2 |
2/6 |
6/3 |
3/7 |
|
B-flat /F |
F/C |
C/G |
G/A |
|
|
音域 |
5→6 |
2→3 |
6→1 |
3→5 |
|
C→D |
F→G |
C→E-flat |
G→B-flat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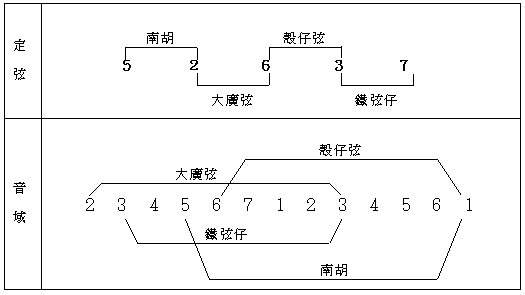
上表顯示了【慢七字】四種伴奏胡琴,其定弦之間有著五度相生的關係。
【七字調】使用的音階基本上是降E大調音階,羽調式,故聽起來接近於C小調。在調高的問題上,還有以下兩點必須特別補充說明的。
第一,野台歌仔戲的定弦通常比內臺或電視歌仔戲中低一個全音,因此,一般的【七字調】樂譜是以D小調記譜,而在本文中皆以C小調記譜。
第二,在伴奏【無頭七字調】(無前奏的【七字調】)時,殼仔弦的指法也可能變成「合乂管」,這種變換指法的原因,是由於演員開口唱出的調門較一般情況高一個全音(D小調),樂師必須配合改變指法。這樣的情形,通常是發生在文場演奏背景音樂時,殼仔弦拉「合乂管」的串仔,其間演員從對白轉至【無頭七字調】,便依循背景音樂的調高來唱,故比平常的【七字調】高一個全音。
(三)「支聲複調」(heterophony)與idiomatic style 「支聲複調」(heterophony)一詞用來描述多聲部音樂的「織度」(texture),是指各聲部的旋律皆循一個基本旋律為骨幹,予以稍加裝飾、變化而成,故各旋律線並行時略有「支聲」,不若單音音樂般整齊,但各聲部的獨立性又遠弱於真正的複音音樂。
在沒有對位、和聲組織的中國傳統音樂中,支聲複調常是合奏的基本原則,這又牽涉到樂曲的可塑性、演奏的即興性與樂器的語法(idioms)。 相較於西洋音樂自Baroque時期開始發展器樂及聲樂的idiomatic style,並有意識地納入作曲技法之中,民間音樂中各樂器因其音域、發聲原理、演奏方式等特性之不同,演奏者在樂曲的基本結構中發展出不同的音樂語法,乃是口語傳統(oral tradition)與「演出即創作」音樂思維底下的產物。因此,從多種樂器支聲複調的演奏中,比較其“異曲”與“同工”,有助於循此歸納出隱藏在樂曲背後的骨幹音。
民間戲曲俗語中對唱腔伴奏有「逢板合,逢眼分,蛇路鰻路各自尋」的形容,斯言透露:骨幹音原則上發生在強拍。又云「起調分道揚鑣,落音異途同歸」,強調出樂句的落音比開頭更具規範性。種種關於骨幹音的問題,都是本文探討【慢七字】胡琴伴奏中所必須思考的。
甚至,支聲複調是否一定要以「骨幹音/裝飾」的邏輯來分析?當骨幹音的解釋行不通時,是否應以其它的觀念來闡明樂曲的深層結構?這些問題,在比較多種樂器各種演奏的可能旋律後,可以有更寬廣的想像空間。
本文中援引兩個西洋樂器伴奏【慢七字】的例子,恰正是因為它似乎比其它的樂器更彰顯出樂曲的深層結構,但它僅作為激發靈感的觸媒,本文仍然以四種胡琴的伴奏分析為主題。 三、托腔與prolongation
(一)Prolongation—synthesizer
本節所探討的是唱腔進行時的伴奏方式,即所謂的「托腔」。戲曲唱腔的伴奏有所謂「裹、跟、隨、閃、領」等口訣,這些都是要配合唱腔的旋律線,但民間藝人在伴奏【七字調】時,採取的是另一種策略,參見以下這個synthesizer伴奏【緊七字】的例子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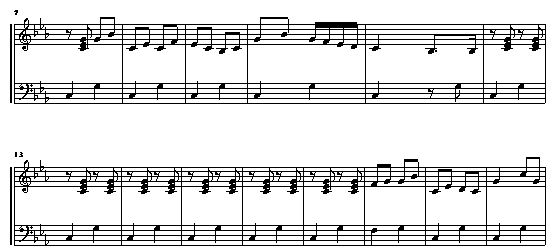
| 【七字調】速度變化及戲劇運用 |
【七字調】唱腔旋律變化之大,幾乎沒有骨幹音可循,在這種情況下,synthesizer伴奏者可以完全不理會唱腔,單純地以主和弦達到托腔的目的,如此音樂依然可以保持和諧、自然,這或許意謂著【七字調】變化不定的唱腔,可以視為音樂結構的表層現象,其背後是以主音為基調的,我把它比擬為一種prolongation,若我們接受Schenker對prologation的"形而上"解釋,也許可以把唱腔視為是以主音為基音之泛音列的展開。
Schenkerian分析中的prolongation觀念,是針對樂曲和聲進行的一種巨觀解釋,主和弦的prolongation在實際的音樂中是隱性的;反之,這裡指出的【七字調】唱腔中的prolongation,則是顯性地呈現在synthesizer的伴奏音樂中。Schenkerian分析是從凝鑄的總譜中揭櫫背後的深層結構,反之,【七字調】的唱腔變化難測,卻是synthesizer伴奏以主和弦來托腔的原因,其能夠和諧地與唱腔並行不悖,正是該處以主音的prolongation為其深層結構的證據。
這裡牽涉到「主和弦抑或主音」的問題,必須在此即刻加以澄清。在傳統樂器伴奏【七字調】時,我只能說它是主音的prologation,而synthesizer的伴奏使用主和弦,是該樂器的語法(如Jazz的打擊樂器一般,"敲"和弦),不能因此判定【七字調】本身有主和弦的和聲構造。
以上的觀察是從【緊七字】的synthesizer伴奏例子中獲得的,但樂曲的基本結構並不會因速度變化、伴奏樂器而有所不同,故以下將進一步以「主音的prolongation」這個觀點,來探討【慢七字】的胡琴托腔。
(二)胡琴的托腔音型
胡琴為【七字調】托腔時,不是以主音的同音反覆來伴奏,而常常是以特定的音型來實踐prolongation。以下以殼仔弦伴奏【緊七字】的例子來入手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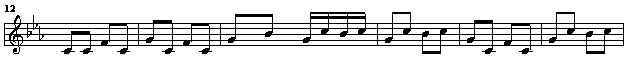
殼仔弦在13-17小節的托腔,可以歸納為下列a、b兩種音型,13及16小節屬於音型a,14、15及17小節屬於音型b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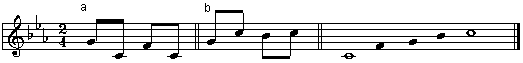
此類托腔的作用宛如Alberti伴奏音型,它賦與【緊七字】穩定流暢的背景節奏,在速度較快時,一成不變的音型能簡潔地烘托出高漲的戲劇氣氛。值得注意的是,此音型反覆於主音、屬音等五個音之間跳上跳下,囿於主音所限的一個八度之內,可視為主音的prolongation。
在【慢七字】方面,各種胡琴中以鐵弦仔托腔的音型化最為顯著,以下是鐵弦仔伴奏【慢七字】唱腔第二句的譜例,其前四個小節為同一音型「6353」的重覆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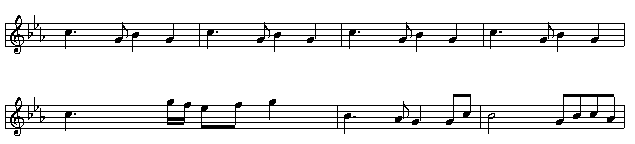
大廣弦托腔的音型與鐵弦仔同為「6353」,但它以各種變奏的形式出現,故音型化的現象並非顯而易見。以下是大廣弦伴奏【慢七字】唱腔第二句的譜例,其前四個小節可視為同一音型的變奏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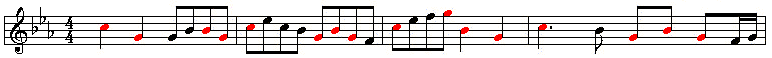
以上兩種胡琴的音域相近,故皆用「6353」之音型來托腔,反之,在殼仔弦、南胡的音域裡,主音比屬音低,這或許是其在伴奏【慢七字】時並無音型化的處理的原因,因為使用「6353」之音型可能不順暢、自然。殼仔弦、南胡的托腔,是各自發展出歌唱性的旋律,與唱腔並行。
四、過門與級進下行
(一)
Conjunct-descent-embellishment—薩克斯風伴奏本節所探討的是【慢七字】的過門,切入點是以「級進下行」來分析它。這個觀點是從薩克斯風伴奏【慢七字】的旋律中觀察到的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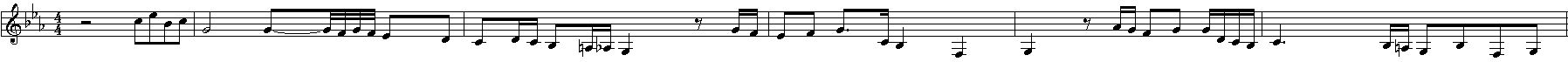
在分為三樂句的薩克斯風旋律中,每一樂句都可視為自g1至G,跨越一個八度的「級進下行的裝飾」(conjunct-descent-embellishment)演奏。「級進下行」是旋律線的自然走勢,或者說,這是人們聆聽旋律的方式(C. Rosen)。級進下行在胡琴中較不明顯,可以說是因為胡琴的音域不若薩克斯風寬廣,下行至最低音便必須轉位,且胡琴的語法不像薩克斯風般偏好級進下行,甚至偶爾用半音階增添慵懶柔媚的風致。雖然不同的胡琴有不同的語法,但以下仍一律從級進下行的觀點來分析【慢七字】的胡琴過門。
(二)胡琴過門中的骨幹音
伴奏【慢七字】的四種胡琴,其過門的旋律各自不同,我們可以藉由比較得到共有的骨幹音。原則上,骨幹音通常發生於強拍,故每小節的頭拍是首先要考慮的點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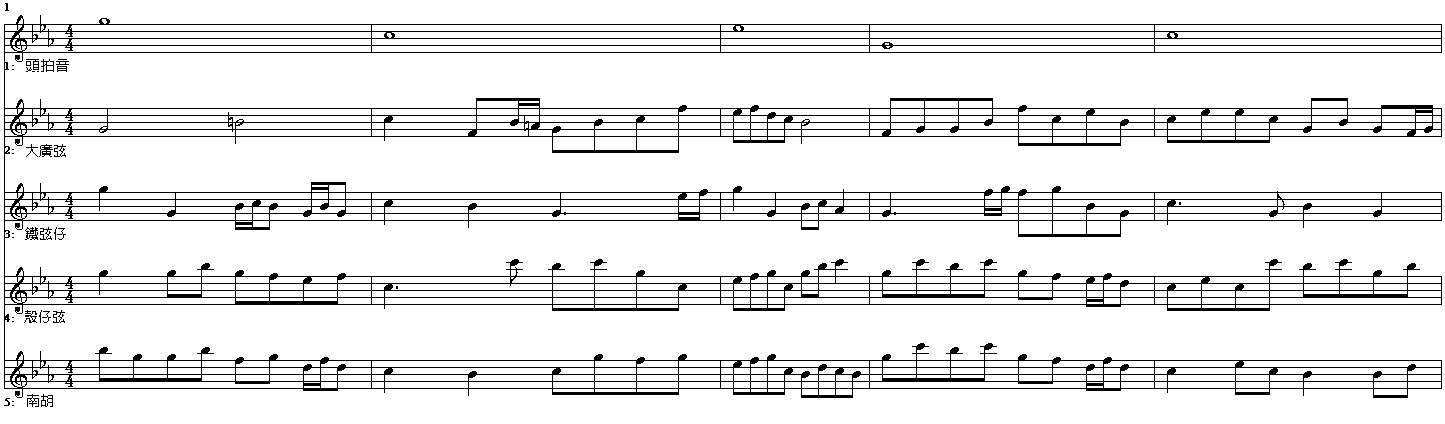
從上譜可以看到,各胡琴的旋律雖然差別很大,但每小節頭拍的音是很固定的,只是頭拍上偶而有倚音,使骨幹音延遲半拍出現,如南胡的第一小節、大廣弦的第四小節。較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小節,除了鐵弦仔以外,各胡琴的頭拍皆為中音Do,究竟這裡的Do是不是可以算作骨幹音呢?從鐵弦仔的旋律來看,第三小節乃是以屬音為主,Do出現於第二小節末拍,只是一個弱起的發語詞,並不具有骨幹音的份量。因此我得到的結論是,【慢七字】五小節的過門,骨幹音只有主音與屬音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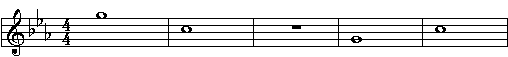
(三)胡琴過門中的級進下行
確定了【慢七字】過門的骨幹音後,以下擬提出一個假設:胡琴演奏【慢七字】的過門,是以級進下行為原則,填充骨幹音間的血肉。將大廣弦、殼仔弦及南胡的演奏譜予以化簡,可以驗證此一假設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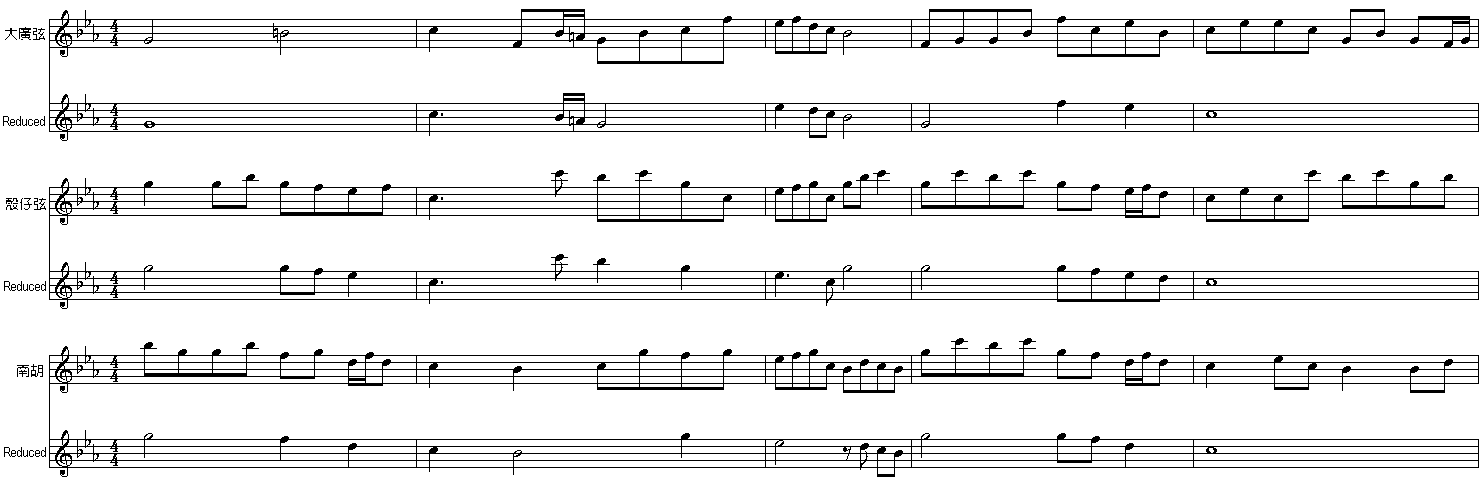
這三種胡琴級進下行的方式,與原譜比較之下,彼此的相似性提高了,但音域的不同仍導致級進下行方式的不同。具體言之,可以區分為兩點來解釋與分析:第一,主音比屬音高或屬音比主音高,第二,音域的底限(即內弦音)如何影響旋律翻高八度的轉位。
例如第一小節的旋律線,殼仔弦與南胡都是從屬音級進下行至主音,兩者相當類似,但大廣弦的音域中因為主音比屬音高,故第一小節為上行跳進。
殼仔弦與南胡的級進下行方式類似,差別只在殼仔弦的最低音為C,而南胡的最低音為Bb,故下行到音域底限時,翻高八度轉位的時機有所不同,如上譜的第二小節。第三小節中,殼仔弦不若南胡一樣級進下行,也是因為殼仔弦欠缺低音的Bb,以上行跳進來連接至次一個小節,聽起來並無下行的感覺,倒是有較濃厚的屬音意味,一直持續到級進下行至主音。
其實,這始於屬音、迄於屬音的級進下行,這三小節乃是以屬音為基調,這與Schenkerian分析中coupling的觀念有點類似:

在鐵弦仔演奏的過門中,它不採取級進下行的方式,這也許跟它音域中存在著一高一低兩個屬音有關。鐵弦仔演奏的【慢七字】過門,係以屬音間的八度跳進為特徵(出現了四次屬音間的八度大跳),因而屬音的意味特別強烈:
![]()
五、
Middleground與Background(一)鑼鼓與終止式
終止式(cadence
)是調性音樂的重要觀念,在【慢七字】這種大小調音樂中,是否也有類似於終止式的樂段之頓挫呢?在上一節關於過門的討論中,屬音級進下行到主音的進行,很容易讓人連想到Schenkerian分析中的Ursatz,只是【慢七字】是單音音樂,不能與和聲觀念底下的終止式產生實質的關連。【慢七字】的過門雖無屬七和弦接續主和弦的和聲進行,但卻有音響豐富的鑼鼓與旋律並行,這促使我構思出「節奏觀念底下的終止式」此一想法。
【慢七字】過門的鑼鼓基本上有兩種打法,節奏型分別為:慢長錘、反長錘。這兩種鑼鼓都在過門結尾的「屬音→主音」該拍點上,予以節奏上的解決。
「慢長錘」平行插入於【慢七字】的過門中,在結束時有一個節奏的變化作為對比:

「孔
匡 台七 台」鑼鼓的最強音在「匡」,次強音在「七」,這一個小節反常的重音位置,致使連接至下一個小節時,節奏上有「懸宕→解決」的感覺。「反長錘」(閃錘)指的是一種六八拍子的鑼鼓,它與四四拍的【慢七字】過門並行,三對二的複節拍關係造成節奏上的緊張感,這個緊張感持續到末一小節頭拍上的主音才獲得解決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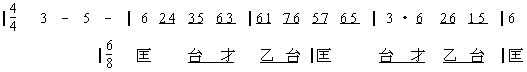
從這兩個鑼鼓的分析,我所要指出的是,【慢七字】的文武場伴奏,賦與此曲在每個過門末一個終止式。於文場,是「屬音→主音」的旋律進行;於武場,是鑼鼓節奏的「懸宕→解決」。用Ursatz 來表示此一終止式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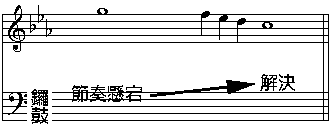
(二)支聲複調與多層次(
multi-layers)分析Schenkerian分析是德奧音樂傳統底下的產物,在本文中,因為分析的對象並非大小調音樂,亦無和聲、複音結構,所以不宜稱為“【慢七字】的Schenkerian
分析”,然而,或許可以稱為multi-layers分析。Schenkerian分析也被稱為multi-layers分析,意即藉由區分音樂作品的幾個結構層次:background、middleground(s)、foreground等,以釐清各個音樂元素之間的關係。以下以【慢七字】的過門為分析對象,區分為五個層次:
| 1 |
Background |
〔D→T〕終止式 |
| 2 |
Middleground I |
骨幹音 |
| 3 |
Middleground II |
轉位後的骨幹音 |
| 4 |
Middleground III |
級進下行與轉位 |
| 5 |
Foreground |
從實際演奏採得的譜 |
如下例為南胡演奏【慢七字】過門的多層次分析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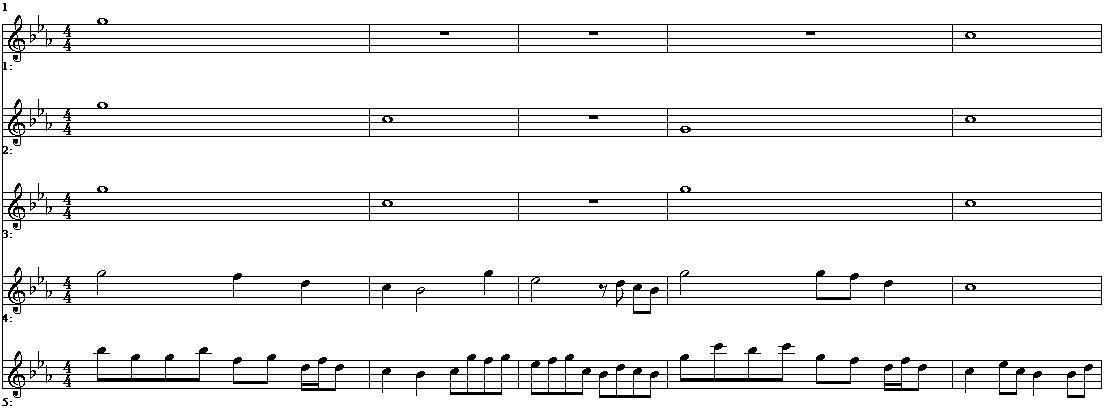
「支聲複調」(heterophony)的多層次分析,有一點與Schenkerian分析不同,它不是揭櫫單一樂曲的音樂結構,而是從同一支樂曲的各種演奏實例所成的集合中,釐清產生支聲複調的種種變數。每往下一層,不僅旋律血肉逐漸豐富,且逐層可能伴隨的分裂,也表示出旋律歧異性的增加。以下詳述每一層的定義與所導致的分裂。
Background只允許最基本的「屬音→主音」終止式。
Middleground I為(各種演奏共有的)骨幹音,不計轉位。
Middleground II為實際音高的骨幹音。從這一層開始支聲複調的“分裂”,因為各個胡琴主音、屬音的高低關係不同。
在Middleground III中,為骨幹音間的級進下行連接,由於考慮個別樂器的最低音,高八度轉位的點不同,因此南胡與殼仔弦於此層再度分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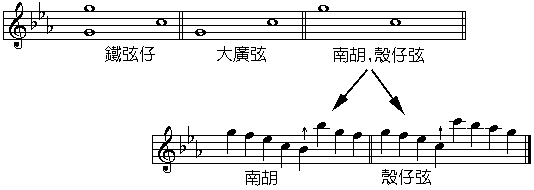
(三)
Concertato medium與tonic-dominant polarization分析的兩個步驟為「化簡」(reducing)與「關連」(relating)。以上多層次分析主要在做「化簡」的工作,本節將注意力集中在【七字調】全曲的background,從而彰顯其「唱腔╱伴奏」的tonic-dominant polarization關係。以下對【慢七字】的前奏到第二句唱腔略做描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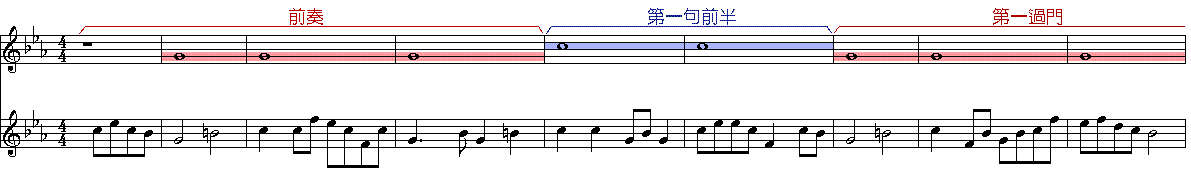

三個半小節的前奏以屬音為骨幹,以「屬音→主音」合理地帶入唱腔的開始。第一過門以屬音開始,解決至主音,接著是第一句的後三字,唱腔常結束在屬音,第一、二句之間的小過門亦承接屬音,以「屬音→主音」接至第二句主音的prolongation。
|
伴奏 |
前奏 |
|
第一過門 | 小過門 | ||
| 唱腔(第幾字) | 一二三四 | 五六七 | 一二三四 | |||
|
Background |
D |
T |
D→T |
T→D |
D |
T |
可見「唱腔╱伴奏」有「tonic╱dominant」的關係,這樣的polarity值得做進一步的解讀。C. Rosen在The Classical Style一書中指出,古典樂派的音樂語言以「調性」觀念最為根本,作者以tonic-dominant polarity一詞來概括十八世紀以來西歐音樂日益強調的「主╱屬和弦」及「主╱屬調」關係。(註二)
從【慢七字】的伴奏分析中可以看到,過門以「屬音級進下行至主音」為background、唱腔則為「主音的prolongation」,這樣的唱奏關係並不是【七字調】與生俱來、一成不變的本質,而是慢慢演化、發展而成的。【慢七字】的過門具有強烈的「屬音→主音」之終止式意味,但【七字調】的前身:【賞花調】、【大七字】、【古七字】、【古早七字】等曲調,其過門並無終止式應具有的頓挫感,它原本只是環繞於唱腔結束音的一個填充物。以下譜例為第一句四字之後的過門(音樂選自宜蘭縣文化中心出版之歌仔戲錄音帶「錦歌類」),黑體數字為唱腔的結束音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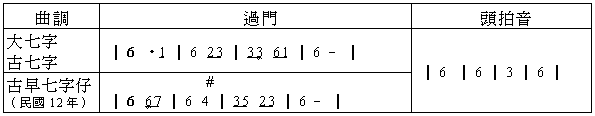
與【七字調】相近的【江湖調】,過門更是固定於主音。【七字調】發展到後來,第一句第四字唱腔的結束音漸移至屬音,tonic-dominant polarity漸趨明顯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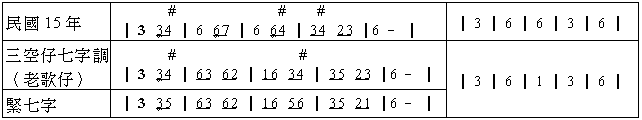
因此我認為在【七字調】發展的歷程中,過門從原本是延續唱腔的結束音:主音,至【慢七字】之過門為屬音解決至主音,唱奏關係完成了tonic-dominant polarization的演化。我在此使用polarization一詞,而非如Rosen一樣用polarity一詞,旨在強調【七字調】中的主屬音在「唱腔╱過門」中被彰顯的"動作",此術語的使用亦不免受到電磁學影響(polarization在物理學中意謂著極化、偏振化)。
詳細來看這個polarization的“動作”,可以跟西方音樂協奏曲作一個比較。
詠歎調(aria)與協奏曲(concerto)都是「獨奏(唱)vs樂隊伴奏」的樂曲型態:concertato medium,在西方音樂史上,兩者的互相影響亦歷歷可見,其也有所謂的過門:orchestra tutti或ritornello。
十八世紀初Corelli的大協奏曲(concerto grosso)自三重奏鳴曲(trio sonata)發展而來,在這些僅略具協奏曲雛型的作品中,orchestra tutti已經被賦與「強調終止式」(to punctuate cadances)的功能(Hutchings1980:628)。古典時期協奏曲與奏鳴曲式結合,這個功能依然相當重要,如呈示部結束的codetta常為cadential tutti。
總之,【慢七字】的過門強調出此曲的tonic-dominant polarity,這在各劇種戲曲聲腔中並不尋常,因為在比較多的曲牌唱腔、板式、小調等例子裡面,過門只是環繞於唱腔結束音的一個填充物(註三),少有強烈的「屬音→主音」終止式意味。
【慢七字】在無前奏的情況下唱出,開頭的前四字只規範出曲子的速度,旋律則依字音有各種變化的可能,拖腔、結束音亦頗自由。或許因為要在樂曲一開始建立起【慢七字】羽調式的主、屬音關係,演員唱出四個字之後,文場奏出屬音級進下行解決至主音的五小節過門,並由鑼鼓加強出終止式的力量,藉此鞏固曲調的性格。換句話說,【慢七字】的唱腔可以起伏變化、充滿細膩的裝飾音,但過門的「屬音→主音」終止式,總能夠使跌宕不羈的唱腔有所依歸。
【七字調】的過門緊束了樂曲的統一感,宛如詩的韻或竹的節,正因為過門穩固了此曲的結構,【七字調】才能夠像竹子般富有彈性、婆裟起舞。
六、結論
本文對【慢七字】伴奏的探討,在一定的程度上挑戰了支聲複調中骨幹音的概念。
【七字調】的唱腔依字音而有極大的變化,尤其在每句的前半段,可說全無骨幹音的規則可循,此時伴奏的托腔為主音的prolongation,但並不能說骨幹音為小節頭拍上的主音,也就是說,“硬梆梆”的骨幹音應由更“縹緲”的prolongation觀念來取代。
前面提過「起調分道揚鑣,落音異途同歸」這句戲諺,其實是道出了中國戲曲唱腔「可塑性、規範性」的奧妙。在崑曲南曲曲牌中(如【懶畫眉】),主腔都出現在句尾,句首常只有音域的寬鬆規範,也符合這句戲諺,但崑曲與【七字調】不同的是,它不像後者有個顯現prolongation的文場伴奏,也許,崑曲南曲句首依字音起伏的旋律變化,根本沒有prolongation的深層結構。
歌仔戲文場的新一代演奏者,常常放棄了以prolongation的realization來托腔的方式,定劇本、勤排練的結果,使他們可以掌握唱腔的旋律,從而以裹腔的方式來伴奏唱腔,這便有點像上述崑曲南曲的情形:伴奏隨唱腔而凝固。樂師如此偏愛包裹、跟隨唱腔的和諧音響,使主音prolongation的本質隱而不顯,對於伴奏聲部的獨立性也有深刻的影響。
在【慢七字】的過門方面,僅僅用主音、屬音這些骨幹音來解釋支聲複調,似乎有所不足——僅以四個骨幹音"裝飾"出20拍的音樂未免太過牽強——本文指出「級進下行」與「終止式」才是過門的深層結構,當然,各種樂器對級進下行的realization是頗為不同的,其中樂師的個人風格也是一大變因(比如說本文中洪堯進演奏鐵弦仔時並無級進下行的處理,迥異於林竹岸演奏大廣弦、南胡、殼仔弦的處理),這些在本文中都無法詳論。
從【慢七字】background的分析中,我指出了「唱腔╱過門」中tonic-dominant polarization的深層結構,從【七字調】的發展歷程來看,tonic-dominant polarity一直到【慢七字】的出現才確定下來,也就是說,文武場在過門所共築出的強烈終止式,是【慢七字】有別於【緊七字】的一個音樂特徵。
本文對【慢七字】的分析止於唱腔的第二句,如第二過門、第三過門等,都未列入分析的範圍,雖然說【慢七字】的過門畢竟只有一種,但第二過門、第三過門的起調,分別承接下主音(主音下方大二度;徵音)、主音,與起於屬音的第一過門,還是有值得細細追究的差異,尤其唱腔第二、四句的結束,文場落音為徵音,在羽調式的【七字調】中究竟意味著調式色彩的變化或僅是屬音的延伸、裝飾,這些問題仍有待做進一步的分析。
七、餘韻
參考資料
中國大百科全書.戲曲曲藝卷編輯委員會
Rosen, Charles
Hutchings, Arthur
Stock, Jonathan
註二:
Rosen所指出的主要有三點。第一,上五度關係(屬音)遠比下五度關係(下屬音)重要,因為在古典時期取得絕對重要性的大調,音階裡只有下屬和弦根音在「下五度方向」,其它五個三和弦之根音都在「上五度方向」。第二,屬和弦(尤其是屬七和弦)至主和弦的進行,成為最重要甚或唯一的終止式。第三,轉調的意義從巴洛克時期的「染色」功能,變成從主調延申出的近系調上的不協和、緊張;主調轉到屬調成為樂曲中深具結構意義的轉調邏輯(1972:23-26)。
註三:
過門為環繞於唱腔結束音的一個填充物,這在各戲曲劇種的唱腔中屢見不鮮,如京劇中的吹腔、【四平調】,或歌仔戲【都馬調】、【三盆水仙】等。在J. Stock的The Application of Schenkerian Analysis to Ethnomusicology: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一文中,這個特徵成為分析越劇【尺調】所得到最重要的結論。